为触摸古法造纸历史温度,赋能非遗技艺时代新生。铜仁职业技术大学“拾光守遗”团队的10名成员在指导老师晏薇娜、昌晏飞、王美会的带领下,踏入了江口县云舍村这片土地,开启古法造纸非遗传承之旅。
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,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和平师傅早已在作坊等候。他粗糙的双手布满了岁月与竹纤维共同刻画的纹路,那是七十二道工序在他生命中留下的印记。杨师傅的声音低沉而坚定,说到:“每一张纸都是有生命的,从选竹到成纸,七十二道工序环环相扣,缺一不可,这不是简单的技术流程,而是我们与自然对话的方式。”
(图为古法造纸非遗传承人杨师傅。潘冬玉 供图)
随后杨师傅脱去鞋袜,赤脚踏入石臼,开始用脚舂臼竹子纤维。杨师傅向成员们说到:“脚比机器更懂得分寸,纤维太粗则纸糙,太细则易破,必须靠人的感觉来把握。”团队成员们轮流尝试,却发现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暗含玄机。脚掌与纤维的每一次接触,都需要将全身重量精准地转化为恰到好处的力度。
(图为实践团成员向杨师傅学习用脚舂臼。潘冬玉 供图)
之后,实践团重点学习了造纸工序中最关键的“荡料入帘”和“覆帘压纸”技艺。杨师傅手持竹帘,在纸浆池中轻轻一荡,手腕灵巧一转,纸浆便均匀地附着在帘网上。“力道要柔中带刚,动作要一气呵成。”在杨师傅手把手的指导下,成员们反复练习这一关键动作。刚开始,成员们不是力道过重导致纸张过厚,就是动作生疏造成纸张厚薄不均。经过数十次的尝试,终于有成员成功抄出了第一张完整的湿纸。
(图为杨师傅讲解“荡料入帘”操作要领。陈垠肃 供图)
(图为杨师傅指导实践团成员操作“荡料入帘”。陈垠肃 供图)
“覆帘压纸”环节更是考验耐心和技巧。成员们需要将抄好的湿纸小心翼翼地反扣在木板上,用手轻轻拍打帘背,使纸张完美分离。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,实则蕴含着匠人们多年积累的经验。“要像对待新生婴儿一样轻柔。”杨师傅的比喻让成员们印象深刻。经过反复练习,大家逐渐掌握了手腕发力的技巧,成功制作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张手工纸。
(图为杨师傅指导实践团成员操作“覆帘压纸”。陈垠肃 供图)
(图为实践团成员独立完成“荡料入帘”。陈垠肃 供图)
制作完成后,实践团成员围坐在杨师傅身旁,聆听古法造纸的现状。杨师傅讲解着传统工艺,目光扫过空荡的作坊——曾经热闹的劳作声已不复存在,如今在云舍村仅剩他一人仍在坚守。纸浆滴落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,仿佛在诉说这项千年技艺面临的传承困境。“现在有机器了,不挣钱,年轻人不愿意学,都出去打工了。”杨师傅话语中满是落寞与无奈,成员们凝视着那些见证岁月的老工具,神情凝重而坚定。
(图为实践团成员采访杨师傅。潘冬玉 供图)
离开云舍,团队成员们带走的不仅是亲手制作的纸张,更有一份关于非遗文化传承沉甸甸的思考。那七十二道工序中蕴含的是一个民族对材料的理解、对工艺的执着、对自然的敬畏。当机械制造的纸张充斥生活的每个角落时,这些由时间与人力共同孕育的古纸,正以其独特的温度和质感,诉说着另一种可能——在快与慢、新与旧之间,非遗文化需要多样性的延续。
(图为实践团成员与杨师傅的留念合影。潘冬玉 供图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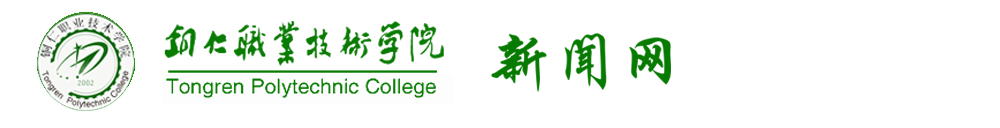








 贵公网安备 52060202000110号
贵公网安备 52060202000110号